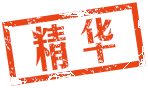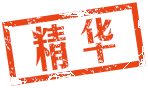九十年代初,有个叫“德竖”的剃头匠,包了几个大队的“人头”,他是个单身汉,以剃头为生。我最后一次见到“德顺”叔叔是在2011年,我们一同走在上坡的路上,他费力地推着永久自行车,我向他打招呼,他朝我笑了笑,又卖力地向前行走了。岁月的沧桑已经很难让我辨认他的容颜,如果不是走在回家的小路上,我压根认不出他来。
“德竖”叔叔从前是个逍遥快活的人,是他最先买得起自行车的。印象中,他总是醉醺醺地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晃荡在乡村小道上,车把上的“商务包”装着他剃头的行当。不知道是不是母亲待人和善的原因,他总是早上到我家蹭饭吃,剃头师傅来了,烟酒不论好坏总是得准备的。他坐在炉子边,边用筷子夹着炉子里的萝卜白菜,边啧啧地嘬着白酒。黑铁锅腾起的烟雾,遮盖住了他的脸,他边吃边喝,直到九点才吃完。
吃罢早饭,他就开工了。父亲坐在靠子椅上,他拿出有些脏乱的围布摊在父亲身上,继而拿出那把贵重的“收推子”,开始了像桑蚕吃叶一样漫长的剪发。父亲茅草似的头发,一堆堆地掉落在围布上,父亲突然间做出痛苦状,“滋”地叫了一声。“德竖”叔叔这才意识到推子不快,扯到了父亲的头发,他拿出一小瓶缝纫机油,滴在推子上,又继续开剪了。
十五分钟过后,父亲的头发终于剪完了。“德竖”叔叔,抖落掉在围布上的头发,喊我倒水给父亲洗头。父亲的头低在盆子里,“德竖”叔打了些肥皂,就在父亲头上揉了几圈。他抓来搭在椅子上的毛巾,就往父亲脸上抹了。父亲的脸揩干净以后,“德竖”树拿出刮刀在椅子上的“荡荡片(一个看起来很脏的布片,好像涂了油在上面)”上荡了几下,就开始给父亲刮脸了。刮完脸,他又掏出小剪子帮父亲剪了鼻毛,整个理发过程才算完结。
父亲剪完后,喊我回来剪。我饱受“德竖”叔扯发之苦,撒腿就跑了。“德竖”叔只好给爷爷刮光头,每次刮光头爷爷总要数落“德竖”叔,“你的手艺哪个茬学来的?连个光脑壳都刮不圆?留的发茬子扎肉”。“德竖”叔只好赔笑,“我这次放过细点”。
由于“德竖”叔剪的头发像狗子啃的,再加上他总是不按月剪发,找他理发的人越来越少。每到过年,他收剪头发的钱,人家都不给,母亲见他可怜,“如数”给了10个月的剃头钱。95年以后,剪头发的地方越来越多,“德竖”叔的生意越来越冷清,尽管他开的价钱很低。后来,只有几个不讲莫斯的老头成了他的“老主顾”。
09年在爷爷的葬礼上,再一次见到了“德竖”叔,听母亲讲,他现在赶场子了(红白喜事的场子,帮人理发、说吉利话,混口饭吃)。“德竖”叔一连几天帮我们剪孝头,好在有酒喝、有烟抽。常言道“百人百性”,“德竖”叔稀里糊涂地过着自己平凡的日子,到老了才有些发慌,原因是忙着攒“防老的钱”给自己的侄子。虽然“德竖”叔手艺蹩脚,却是一个十足的“老实人”,遇人爱打招呼,总是堆着满脸笑容。真心地希望这个“糊里糊涂”的剃头匠能安稳地度过余生,好人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