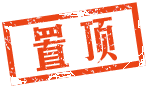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梦中的绿洲! 于 2015-3-17 10:33 编辑
《缺“火”的诗坛》
——当下诗歌现状分析
文/李犁
当下的诗歌是近三十年来最平静也最繁荣的时期,各种流派相互宽容,并开始了融合与创新。但是在文本进步的同时,另一种忧虑涌上心头,那就是过分的个人化和反崇高,让诗歌格局变小,同时伴有软冷乱。诗歌中没了志向和情怀,自然就多了冷漠和灰暗。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缺火的诗坛,没有了熊熊大火,诗歌也就没有了气血贲张和荡气回肠。火即情怀,包括情怀派生出来的理想、道义、激情以及侠肝义胆。所以诗坛需要情怀之火烧出对人性的大体恤,生命的大关怀大温暖的作品。情怀看似很大,其实很小,小到看不见,而像一种气体弥漫在诗人的身心里。一声叹息,一滴眼泪,对卑微者深情地一瞥,对邪恶者愤怒地一瞪,都是情怀本能的显现。所以陆机在《文赋》中对作家提出的重要要求就是:“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以凌云。”现在诗歌忽视了志,过分强调智,结果只能是技术上升,格调下降。所以诗歌不能抽离情怀,呼唤情怀就是要点燃诗歌中的大火,并让它照亮诗坛。
为了避免概念化,下面结合诗歌的文本实践谈谈当下诗歌应具备的五种“火”。
淬火:“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标题引用的是曾经给香港富士康打工的青年许立志写的诗歌,诗的前半段是“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作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读这样的诗歌,很多人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这是一颗单纯的心被冷硬的工业齿轮啃噬时的呼喊,是一个无产者为了谋生甘愿被海外资本家榨取生命的真实控诉。这样的诗句犹如烧红的铁投到冷水里,那疼痛时冒出的丝丝烟缕和嗞嗞声响都是自动生成的,而非那些隔靴挠痒的无病呻吟。所以真正的诗歌源自于心灵,是心灵被刮下来的血和肉,是生命上生发出来的新生命,有着真切的灼烈感。淬火,强调的就是生命与现实遭遇、碰撞的瞬间迸放出的火花和感知,是滚热的心在现实中冷却显形的过程。所以淬火的诗歌核心是真,真的事实,真的感觉。写淬火的诗歌就要剔除诗歌中虚妄的东西,让诗歌攥紧,像金属在浓缩和凝聚,挤出所有的杂质,让钢变得纯粹和坚硬。整个写诗的过程就是提纯的过程。
本来真实是诗歌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后来却被诗人给弄丢了,而且诗人名气越大诗歌越空洞。相反在一些声名不太显赫的诗人作品里,却常常感受到快刃剔骨般的真实和直接。譬如最近走红的余秀华的诗歌:“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不管她的诗歌争议有多大,但是你必须承认她诗歌中的淬火感,一种冷与热相撞时灵魂的不寒而栗。同样揭皮般疼痛和真切的还有何三坡的《姐姐》:“那个生养了5个孩子,总被姐夫打倒/又爬起来的人/是我的姐姐……//那个像一株茅草/一阵风就吹倒在田里的人/是我的姐姐/生病了,在医院门外站一会儿/她就回了家”。无独有偶,颜梅玖(玉上烟)有一首写《哥哥》的: “……你说你恨极了我高傲的样子/哥,不是我有意抬高视线/哥,我一低头/眼泪就流出来了”。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都是自己的手足,面对亲人,诗歌的触角自然会深入到骨肉中,不仅真,而且情入骨髓。只是前者是白描,后者是倾诉;前者是典型性,后者是个人化。同样的疼痛,与前面的许立志和余秀华的诗歌比,他俩的诗歌多出一层对他人的关怀和深情,这就增加了命运的深厚感和广泛性。
这就是情怀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诗人的写作。有情怀的诗人能从自己的疼痛上升到同情别人的泪,甚至推及更大的空间和更广的人群。这就让诗歌有了悲悯,有了辽阔。例如李南有一首诗叫《我去过许多地方……》,在写了爱庄稼农舍、方言和农民后,她写道:“这就是我的祖国:/迷信和战争走过它每一寸肌肤/这就是我的人民:/在风中,他们命若琴弦”。诗歌像挖掘机在开掘,一下下,在深入在逼近核心,最后把真相端出来。这里诗歌是倾吐,也是凝聚;是温软的泪水,也是冷硬的铁。诗歌的形成过程,就是把自己情感的烧热,再经过锻打,把滚热的情感放进冷静的理性之水里淬火成型,最后就成了尖锐的剑,或者子弹,直指心灵。
所以,淬火的诗歌都伴随着思考并最终走向思想,也只有抵达了思想,诗歌才有了骨骼,有了心脏,有了品格,才称其为真正的诗歌。因为诗歌是诗人对世界的态度和看法,好的诗歌必须从真实中抠出真理,把存在引入到哲学的高度,诗歌形而上的解谜功能就在于此。所以陆健在他的长诗《美轮美奂小诗人之歌》中用理性为现实号脉:“诗歌的手臂已经脱臼/她扶不起那个叫作现实的大脑袋/人民被催肥,肚腹里装满困顿、焦躁/肠胀气、前列腺炎,等等。但人民/还没胖到不会游泳也沉不下去的程度……唯有自尊,说出来我就自责就想哭/唯有自尊像一块还不太脏的粗布/我们用它做成旗子还是做成短裤?”这是从现实中淬火出来的大地之痛,时代之痛,更是诗歌之痛。它太大了,大到整个存在都充满了痛感;它又太小了,小到只剩下了针尖要挑破这个虚肿的时代。这是用理性来统摄纷繁的世界,也是用形象来化解抽象的认知。诗歌在这里是一剂药,更是一柄剑,它们一起为这个浓胀的时代放血、消炎,让社会重回理性和道德。在犀利和沉痛的背后是诗人深沉的爱和终极体恤。
因此,淬火的诗歌就是写诗人对生命和现实的疼和爱,还有忧与乐。不论淬火之诗是痛还是怒,诗人写作的起源都是爱,最终还是要走向爱。真实是诗人之爱的第一步,而将爱推向更广远的时空,将是诗歌更高的追求。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节——
炉火:“把我眼中的灯盏取走”
写下炉火两个字,我情不自禁想起很多年前读到的李南题为《呼唤》的一首诗:“在一个繁花闪现的早晨,我听见/不远处一个清脆的童声/他喊——“妈妈!”/几个行路的女人,和我一样/微笑着回过头来/她们都认为这声鲜嫩的呼唤/与自己有关//这是青草呼唤春天的时候/孩子,如果你的呼唤没有回答/就把我眼中的灯盏取走”。这是一首被爱照耀得内外通透的诗。即使是严冬,读着它,也会有炉火在血管里流淌。一股暖流会从内向外蔓延,直到冰雪消融,包括万物之间的屏障和距离,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雾霾。这一切都归于也集中在听见了孩子的呼唤,几个女人转过头来的一瞬间。这是诗意从庸常的生活中耸起的瞬间,是炉火被点燃,爱的嫩芽在绽放,整个世界被制纯且温暖又柔软的瞬间。以至于二十多年过去,我一直记得初读此诗的感觉,那恰是无数的火焰在心里扑棱着翅膀,犹如早春的麦苗一夜间覆盖了无垠的大地。
我冗长地写对这首诗的感觉,是想说明具有炉火般品质的诗歌魅力,这也是一种情怀,是情怀的潜动力让炉火自然地发热,并催生着诗歌自动地绽开。所以有着炉火一样情怀的诗人,都对万物怀有虔敬之心,并保持着明亮的心态。让温暖日常化经常化,把感动感恩融化在平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间,并成为一种习性和习惯,而不是专门在特殊的时间和事件上才特意地让自己伟大地点燃。怀揣这样的胚胎,诗人们会激动兴奋,随时能发现诗,也随时能诗,随时把热量传播出去。诗人郭晓琦就是在这样情绪的鼓动下,发现了《一个瞎子的美好春天》:“……一个瞎子,他感觉到他的老骨头/也有了拔节的声响——/他感觉到,有一条刚刚睡醒的河流/盲目、冲动/在他的身体里横冲直撞——//整个春天,一个瞎子喋喋不休/他指着头顶,对靠在墙根的几个老伙计/大声嚷嚷:你们看看,看看/这春天的天空,蓝得多像天空——”
一个瞎子怎么能看见天空的蓝?这无疑是幸福的通感在濡染。这是一个瞎子的美好春天,更是诗人身体里横冲直撞的热情和炉火在繁衍和外化。读这样的诗歌,会浑身发热,内心亮堂。这就是正能量,这在冷酷又冷漠泛滥的诗坛显得弥足珍贵。每个写诗之人应当珍惜,并对美好和万物永葆敬爱敬畏之心。诚如徐俊国在《一个早晨》中写的:“……如果碰见一条小河/要跪下来 要掏出心肺并彻底洗净/如果非要歌颂 先要咳出杂物 用蜂蜜漱口/要清扫脑海中所有不祥的云朵/还要面向东方 闭上眼/要坚信太阳正从自己身体里冉冉上升”。这是对待美好的态度,谨慎还要虔敬。因为美如神,圣洁不可亵玩,这也给出了保持炉火燃烧不灭的条件和理由。同时也给炉火的诗歌加重了颜色,让爱意奔流的诗歌有了深沉和思考。因为温暖不能盲目,明亮也不能轻浮。爱意中要有方向,热量里更要蕴含能量。因此诗人不能被炉火烤昏了头脑,要爱得合理,暖得有理。这一切一定要在诗中加进思,而思一定要思本质,思情感和生存之根。所以李南在《羞愧》中写道:“……羞愧啊!面对古老……的国土/我本该像杜鹃一样啼血……”。如果对祖国没有深入骨髓的爱,无法写出这样啼血的文字。诗人通过这样的诗句在自责自省,更是自救。这是炉火在冒烟,爱得已经疼了,痛了,病了!再看陆健的诗歌:“……把爱接通到人心里去,以免缺血/紊乱、梗死。接通到企业、机关里去/单位也许就开始有点人的样子//有爱的人是从内向外的美,尽管遭到/权力和金钱诋毁。政府如果无法让爱像/货币一样流通,它就该天天给自己放假……”这是继续给诗歌里加思,给炉火中加煤,加镭,不仅让火大起来,还让它有爆炸的可能。诗歌不仅暖人烤人,还给人方向和力量。诗歌也因思的加重变得深厚而寥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