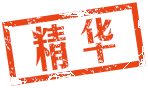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随州之梦 于 2014-7-18 18:39 编辑
《永远的神韵》后记 《永远的神韵》付梓,我有一种很温暖、很圆融的感觉。甲午年过去就是乙未年。我是乙未年出生,马上就要走过一个甲子,我确确实实有些不敢相信。我出生在随州古城一个铁匠之家,家境很是寒微,在我的记忆里,能吃饱米饭就是人生的大幸福。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不太记事,大人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扒家,也有些霸道。 我确确实实不记得这些事,根据大人们的描述,还原当时的状况。我四五岁的时候,就晓得到农业队的菜地里,去抢菜根和老菜叶。我小时候住在随州城南关坟茔附近,就是现在的随州中心人民医院旁边。在我的记忆里,县医院只有天主教堂和旁边的一两排平房,现在的医院基本上都是二街农业队的菜地。老县城三个街道都有农业队。农业队收菜的时候是用刀子砍,不是连根挖,田里就会留下一些菜叶和菜根。看到大人去捡,可能我跟在后面也捡了。老菜叶和菜根洗干净了,剁碎糊一点面,是可以吃的。大人们说我霸道,就是说我拔过但没有拔起来的菜蔸,谁也不许再拔了,谁拔起来了我会撒泼打滚要来。别人看我那么一个小娃子,叹口气也就算了。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经常是煮碎米饭吃,但还是有许多的快乐,躲猫猫的时候偷偷摘生产队的黄瓜、香瓜。今天的中心医院住院大楼就是建在随州的古城墙上,城墙上种着桃子、苹果、梨子、枣子。照树的是个老头,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些躲猫猫的娃娃。但我们不怕他,有跑得慢的被他逮住,也不过训斥一番。那时候,一斤粮票能买两斤碎米,碎米不是谁家都能买到的。需要找许多关系才能买到。我的爸爸会用打铁的吊锅煮碎米饭,那饭吃的满嘴跑,多数时候是煮稀不稀干不干碎米饭,现在已经忘记了那种味道。倒是城墙内外的瓜果却有一年又一年的快乐,让我时时忆起。 我的碎米饭还没吃出味来,初中就毕业了。下乡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岁。下乡知青的头三个月,吃的是45斤供应粮,顿顿吃上米饭,沾点盐,就香的不得了。后来,和农民一样去抢工分粮,十几岁的娃娃,肯定抢不过别人。我记得1972年的冬天生产队出外工挖渠道,我们生产队小,那一年出外工是五个人每人半斤米,煮在一口大锅里。挖渠道是很下力的活,放工后,我把锅盖一揭开,两斤多米的饭只盖住了锅底。我说:“怎么只煮这么一点点米?”做饭是轮流的方式。做饭人说:“这是两斤半米,我当他们的家,你吃完了,我们莫事也不找你要。”我一辈子也记得,那是一顿真正的饱饭,吃完锅巴之后,我还喝了两碗米汤。 做饭的郑老头说:“十几岁的娃子,下这么大的力气,正长身体的时候,又冇得油水。遭孽呀。”他自己说只当过国军的班长,队上的人说他当过国军的军官,多大的官说不清。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那天晚上,他死不让我睡,说我吃多了,睡早了不好。他告诉我,村上的人都晓得城里的娃子,这么一丁点就自己做家顶门户,不容易。也晓得是你们知识青年偷的鸡子扯的菜,剜的红薯,骂几句就过去了。公社的知青干事来的时候,冇得一个人说你们的拐话,就是想到你们遭孽。 这些事想起来有些苦涩,但更多的却是温暖。我的父老乡亲厚道而宽容伴随着我的成长,这种温馨时时刻刻滋润濡养着我,让我的身心也有了温暖,复述这些细节,其实就是想让这种温暖滋润濡养更多的人。我一辈子没离开随州,从随州普通市民家庭,走向社会,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轰轰烈烈。乡亲们送我读了随县师范,从乡村教师到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到专业创作员,最后还被随州的父老乡亲搀扶成领导干部。 在无边无际的空间和不知起始、永无尽期的时间里,任何个体生命,来到这个时空都是那么偶然,也是那么珍贵。人生百年,是漫长的时光,未来可能能够一百多年,然而和历史、宇宙相比,一百多年也只是那么微不足道的瞬间。在一个甲子的时候,我感到生命的珍贵,越是珍贵,越是要知道感恩。感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来源于祖先,祖先的生命来源于这片天地。随州这片土地就是我另一个层面的父母,今天我用这本《永远的神韵》来感恩随州。 这份感恩得益于自己分管文史工作。我认为文史由文化和历史两个部分组成。文化的核心是爱与善良,有爱与善良就会有“仁义礼智”。孟子说:仁发端于恻隐之心,义发端于羞恶之心,礼发端于辞让之心,智发端于是非之心。随州人“生活的样法”里肯定蕴含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每个随州人的生活中就蕴含着这“四心”。如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就一定能有许多发现。能把感恩情怀当做一种做人的基本准则。就能从普通平凡中发现伟大和崇高,是因为心中对这片土地有了敬畏,这种敬畏是一种尊敬到生怕弄坏了境界。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爱,就自自然然能从普通和平凡中发现许多神奇。 历史是由历史真实和历史观构成的。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人们对社会、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对于随州的历史我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我觉得认为随州的社会存在,决定着随州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关于随州炎帝神农故里的重大问题,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能够很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炎帝神农是人类即将跨入文明门槛之前时代的文化英雄,文明的门槛就是中国的国家建立。中国断代工程已经完成,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建立时间。文明的建立是文明的各种元素已经齐备的结果,炎黄传说时代,就是国家的各种要素已经齐备的时间。这个时间既不能早,也不能迟。云南元谋人早,距今180万年,元谋人也有文明的元素,因为这时人类已经从树上下来了,直立起来、走出丛林,手握树枝,驱赶野兽,谁说这树枝不是工具?能使用工具的人当然有文明。但这时不是人类的文明时代,因为文明的各种要素没有完全齐备。专家们认定国家的要素基本成熟最早不过仰韶文化后期,最迟不过龙山文化早期,也就是距今5500年——4500年,距离夏代的始年1000年前后。这就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来历。 随州5000年前后的历史真实,是农耕文明已经十分发达,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这是随州的山水地形、环境生态所决定的。而且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用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随州地区有一个先进的农耕部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余秋雨先生进一步说,生活中蕴含着价值,很多人认同这种生活和价值,并形成共同体。所以他对文化的解说是三个核心词:生活、价值、共同体。 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随州陶豆的北斗七星雕刻、太极图案纺轮,是5000年前后历史实物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存在就是随州先民圆融和谐思想意识的反映。叶家山许多文物的和谐圆融思想意识、季梁“民为神主”思想就是远古圆融和谐思想意识的延续。 我认为自己是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因为我是以大量历史实物存在,来表明自己对这种实物的“认识”和“判断”。年轻的时候,读过几本历史文献,就感到随州的炎帝神农,有一百多种典籍,应该很厚实。年纪大了,看到许多地方也能拿出历史典籍,方知必须用历史的真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才叫学问。我没能生在读书的时代,读过那几本书,要证明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的唯一性,有很大困难。我就从网上的网民提出的问题,开始思考问题。回答不了,就证明随州炎帝神农文化的接受度不高。我为了提高这种接受度,会花很大的气力,努力说明自己的观点。我从不认为网上的问题荒谬,网民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如果能尽可能丰富的事实,来证明我的“认识”和“判断”,取得别人的共识,是人生一种乐趣。 我的很多认识是站在提出问题的人角度,去思考的,尽可能用他的人生经验来回答。从自己的心灵出发,走进别人的内心,就有可能找到跟别人相通的地方。如果连自己都没有被充分说服的观点,就要别人接受,是霸道和无知。今天,别人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接受你的认知,就不可能形成共识。其实形成共识,就是一种将心比心的过程,所以我尽可能用别人听的懂的话,来阐述随州文化。随州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地域文化,随州地域的唯一性,也就证明了随州文化的唯一性,然后用这种唯一性,解说它在荆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一步解说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州文化的核心是炎帝神农文化。有人觉得这个重大课题,不是一本书就能说得清楚的。实际上这是对炎帝神农文化的内涵理解的分歧。关于炎帝神农文化,群众有自己的认知,专家学者有自己的理解,领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做一种融合与调解。比方,普通群众认为炎帝神农就是一个具体的人,由生于何时何地何日,死于何时何地何日,清楚得很。专家学者感到炎帝神农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有蛮荒走进文明时代的文化英雄。政府希望能让这两者能为自己所用,“世界华人寻根节”的举办,采用民间传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是炎帝神农的诞生日,活动中庙会更多的是敬重民间的炎帝神农文化认知。炎帝神农高层论坛,论述的是专家学者对炎帝神农文化的理解。专家学者的炎帝神农文化概念与普通群众认知的炎帝神农文化概念,两者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相容的地方。如果放大其中不相容的地方,就带来了混乱。这种混乱不光是两者的融合出现了问题,也降低了炎帝神农文化的价值。 不能觉得普通民众心目中的炎帝神农文化认知,有学理上说不通的地方,就贬低其文化价值。恰恰这种情况正好说明炎帝神农文化在人民心中地位的崇高。人民群众感恩自己的衣食住行,从何而来,当然是从自己的祖先那里来的,所以就把人类的所有的物质创造、精神创造功绩,归功于自己的祖先。当无数的美好归结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会有许多说不通。如果站在人民群众敬仰自己祖先的那个角度去理解,这种种的不通就全通了。 正是有了普通群众的无限敬仰,才有了随州古代的“至今神农庙,年年赛村鼓(《随州志》)”的民俗,也就有了今天的祭祀大典,它被列入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明“庙会”到“祭祀大典”有明显的延续,这是一种“活态传承”。庙会让炎帝神农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也让老百姓有了炎帝神农文化的记忆,人民群众有了炎帝神农文化的情怀,节庆就成为人民的盛会。节庆用一种仪式来安顿、抚慰自己的灵魂,探访久违的祖宗和先人,实际上是从东方文化的发源地找回民族的深厚情感,找回断裂的文明。 专家学者认知的炎帝神农文化有更多的理性,从字面上包含着“炎帝”、“炎帝神农”、“炎帝神农文化”三层。我理解这三层是有区别的,“帝”不是群体,只能是个体;“农”不是个体,必须是群体,应为男耕女织最少也是两个人;“文化”有一个核心,就是共同体,人口很稠密的时候,才能形成共同体。专家学者定位的“炎黄”时间来看,国家建立前的千年左右,也就是距今5000年。国家建立的各种要素,通过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因素累积到一定的厚度,这时已经到了发生质变的时候了。这就是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也就是说,炎帝神农的出现不是越早越好。出现的早,只能是准备阶段。就好像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出现,绝对不是共产党,但为共产党的建立做着准备。 炎帝神农是南方的天帝,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域指向,这个指向牵引着我们的思维走向中国文化形成的多元。这种多元让中国文化呈现出成长的态势,多元的不断融合反复为中国文化这个主体输送着营养,这是中国文化具备永久生命力的根本。南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稻谷的种植,稻作农耕是一种精细农耕,这种种植方式衍生出的三个因素,对于中国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是聚、二是序、三是理。稻谷种植必须聚集更多的人,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稻田成为良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就要良好的社会秩序;稻谷的种植要按照稻谷的生长规律,就有极大的增产潜力,就促进科学理性的发展。 随州恰恰是种植稻谷的最佳地域,说这话许多人也许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袁隆平是当今世界的杂交稻之父,他对世界的粮食贡献令全世界仰望,说他是当代的炎帝神农一点也不为过。他和他的团队在中国所有适合种植稻谷的地域都有试验田,其中产量最高的出在随州均川镇的100亩。我曾向相关部门建议,请袁隆平先生在炎帝神农高层论坛宣读自己在随州均川镇杂交稻试验田的实验数据,这个数据具有重大的指标性意义。他有没有常驻随州,已经不重要,他的团队常年有人在指导随州农民按照袁隆平的稻谷种植方法,实际上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随州人的内心深处。今天我们祭祀炎帝神农,绝不是要延续炎帝神农那个时代的的生活,而是继承这种生活中蕴含的价值。 《永远的神韵》主要是解读炎帝神农文化在随州的发生发展,随州的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以为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农耕生活,这就必然与炎帝神农有某种关联。《台湾印象》一文看起来似乎与炎帝神农文化联系不紧密,组织上安排我担任随州市炎黄研究会会长一职,市委书记代表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特别交代,炎帝神农风景区会被授予海峡两岸的交流基地,随州的炎黄文化研究,要在夯实这个基地上动些脑筋,因此,我写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被《中国报告文学》刊载后,其中部分章节先后被多个刊物刊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开了一个头。 我对市委书记说:我感到自己是炎帝神农文化的最大受益者,炎帝神农搀扶我走过生命的大坎坷,组织上安排不安排我担任这个职务,我都会感恩炎帝神农。何况随州文化的研究是一件积善积福的事,《周易·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做这种积德行善的事,恩泽及于子孙。《永远的神韵》的出版,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圆融温暖感觉,更是生命的活力。一个甲子六十年,走过一个甲子的人是一种成熟,更是一种觉悟。所谓成熟就是六十岁的人对利益的得失应该看得谈一些,这种看淡就是一种大成熟;所谓觉悟就是觉察思考,能够领悟生命的意义就是觉悟。能获得这种成熟与觉悟,就一定能让自己的生命的品质质量得以提升。
2014年 |